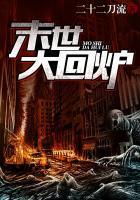笔尖小说网>乱世春秋绘 > 第9章 最是人间烟火气(第7页)
第9章 最是人间烟火气(第7页)
蒲团上的老者忽然出声:“后生可要猜谜?”
他走上前,说道:“好。”
摊主点头:“请。”
慕廉看了一眼娘亲,又看了看灯谜,低声道:
“萤火虽弱,亦可为夜行人掌灯。”
慕廉提笔,他写得极慢,笔画间透出一丝迟疑,终是落笔如下:
——抱朴子曰:言宁为太平犬,心灯照寸土,微愿托苍生。若燃尽此身,万户可长明?是为愿,亦为——
言罢掷笔,却见墨汁飞溅处,最后一字竟断成两截。
摊主沉吟片刻,长叹一声:“一字断尾,借他人意未竟。”
道袍女子遂的轻笑。
慕廉没有辩解,只默默收笔。
远处城楼传来亥初鼓响,沉沉鼓声穿过夜色,宛如一声悠长的叹息,惊起天边残星几颗。
慕廉转身推着轮椅欲离开天禄桥时,忽觉怀中微凉,低头一探,竟多出一枚龟甲符。符甲古旧,其上有一字隐隐可见——“悔”。
他猛然回首,却见摊主、道袍女子早已不在,唯有那盏孤灯之下,灯谜红笺空悬,河灯数盏,随风飘摇而下,远远望去,仿佛一道星河坠入尘世。
狐面女子,太极袍影,已如青烟般消散在风雪之间。
娘亲静静坐在轮椅中,脸上戴着那只兔子面具,青玉小剑簪上的苏穗子在夜风中微微晃动。
慕廉默然良久,终是推着轮椅离去。他低声唤道:“娘亲,咱们去放河灯吧。”
妇人没有回应,眉眼如旧,仍是沉静如水。
可慕廉却觉得,她似是听见了,只是未言。
于是他笑了笑,推着轮椅,沿着石板街一路北行,朝城外的清河口而去。
夜风渐冷,街巷中灯火稀疏,偶有几家夜摊尚未收起,油锅里炸物的香气混着胡麻味儿,顺着风飘得老远。
慕廉闻着那味儿,忽然想起小时候冬至夜里,娘亲煮的糯米团子,里头包的不是馅儿,而是细盐炒芝麻和一撮红糖。
他轻声说道:“娘亲还记得吗?那年冬至,我们炉子坏了,我捧着个破陶罐烤手,您却硬是用酒精灯煮了一锅汤圆,说‘冻也得吃,年节不能亏了口福’。”
话音落下,妇人目光微动,手指似有意无意地摩挲着兔子面具边缘。
慕廉心头一震,步子不由放缓。
清河口到了。
这是一处开封城外的老码头,白日里人来舟往,夜里却静得很,只有潺潺水声、偶尔几声鸟鸣,和远处渔火点点。
今夜河边却格外热闹。
因年尾大集,城中百姓多有放灯祈福之俗,此时河岸边早已聚了不少人。
孩童追逐嬉戏,妇人倚在男人臂膀上低语,老翁则捋着胡子,轻声念着灯上的祈愿:
“愿我儿科考高中。”
“愿家中老小平安无虞。”
“愿来年丰收,莫遭蛮患。”
慕廉推着娘亲缓缓走至人群边缘,避开喧闹,选了一处稍静的河滩。
他从衣襟内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河灯——是用竹篾扎成的六角灯座,薄纸糊面,上头描了几笔梅花,一盏灯芯静静躺在其中,已蘸了香油。
他又点出第二盏,是为娘亲准备的。
灯面上写着一个“安”字,笔迹歪歪斜斜,分明是他亲笔所书。
他心有些乱。
“我写得不好,娘亲莫笑。”
娘亲依旧不语,却缓缓抬起手,食指指向那盏写着“安”字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