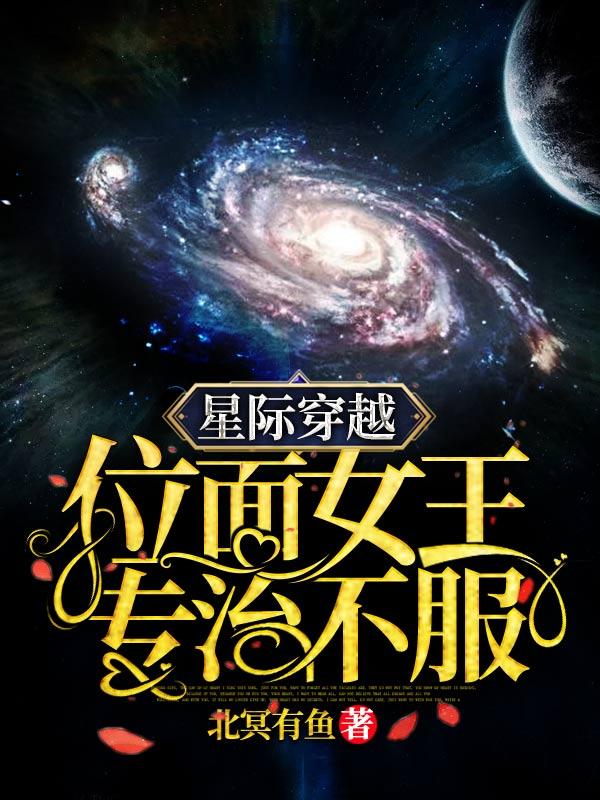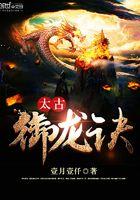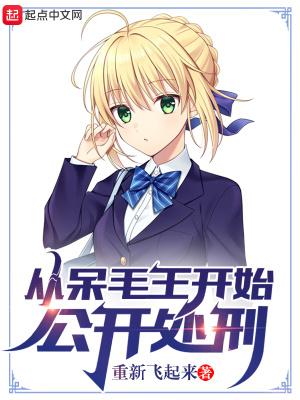笔尖小说网>重启人生,我用金钱碾压一切 > 第九十二章 自治之门系统低温运行(第2页)
第九十二章 自治之门系统低温运行(第2页)
因为这本身就是自治的一部分。
允许质疑,允许失序,允许不完美。
那天晚上,他独自走进江南老城区一座小型社区调解中心。
那是灰域辅助模块试点之一。
中心主任是位五十多岁的妇人。
她见到秦川时,没有多说,只是递给他一份记录表。
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近三天居民自发提交的行为评分自检反馈。
有人记录了自己迟到的原因。
有人写下了自己帮邻居修水管的小事。
有人坦白了自己一次轻微争执的过程。
没有系统评分。
只有自我叙述。
秦川翻到最后一页。
一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写道。
“如果不是因为我可以自己告诉系统,我为什么走慢了,我可能永远不敢说,我其实是腿疼。”
那一刻,秦川明白了。
灰域不需要一直看着人们走得多快。
它要做的,是在他们停下时,仍然愿意告诉世界,自己还想走。
清晨五点,江南的天边泛出一丝浅浅的蓝光。
灰域系统主控后台数据显示,全球路径自治运行已持续稳定超过四十八小时,行为波动幅度维持在可接受范围内。
数据曲线平滑得近乎优雅。
但秦川心里很清楚,这种平滑,不是系统强制结构带来的。
而是社会自身在缓慢、微小但真实地完成一次重构。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评分主导下的结构塑形。
这一次,是人群自己在试探、调整、磨合、缓冲。
他们在灰域回响提示下,自己选择向秩序靠近或远离。
不是被迫,不是被指引。
而是真正的自我协同。
那天下午,秦川没有开例会。
而是独自带着一个随身终端,走进了江南大学城附近的一家青年创业空间。
那里,正进行着一场小型的灰域自治体验分享会。
二十几位年轻创业者、社区志愿者、独立艺术家和社会观察员坐成一圈,正在讨论灰域自治回响机制对各自生活的影响。
没有官宣,没有稿件,没有控制。
只有真实的声音。
一位做城市微景观改造的青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