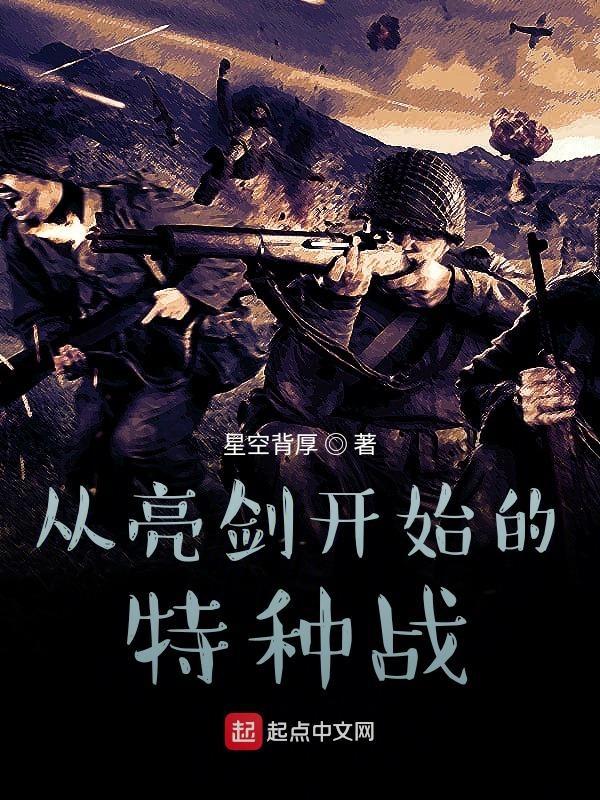笔尖小说网>椒殿深锁薄情种 > 第76章(第2页)
第76章(第2页)
他摇了摇头,凝视她的眼睛,神情依恋柔软,就像看着婴孩的母亲,又像看着母亲的婴孩。
赵濯灵少见这样的他,一时愣怔,情不自禁地靠了过去。
——
内教坊门前跪了几排男男女女。
“拜见贵妃。”
赵濯灵抬手微笑,“都快起来,许久未见,诸位可好?”
为首的内人颔首应答:“谢贵妃关切,奴婢们一切安好。”
众人让开一条道,迎赵濯灵进殿。
她边走边问:“你们近来排演什么?可有新曲新舞?”
“彭伯新谱一曲,贵妃不妨听听?”
“好啊。”
赵濯灵落座后,宫女上了食饮,此间,乐工就位。
一中年男子抱着筚篥,向上座行礼,“彭伯见过贵妃。”
“免礼。”赵濯灵示意他坐下。
有虞人的地方就有彭伯的音乐,他足不出京,谱的歌谣却传唱于四海,他是最知名的乐工和歌者,无数诗作经由彭伯作曲而名声大噪。
多年前,赵濯灵入京赴任秘书省,特意拜访彭伯,他是大忙人,穿梭于皇宫和豪宅贵邸,最后还是广陵公主引见,两厢才见上了面。二人称不上一见如故,但几次来往后,也生出惺惺相惜的忘年之谊。
筚篥声音清亮,多含悲意,一如荒凉大漠中哀咽的夜风。彭伯是筚篥名家,所奏更摄人心魂催人泪。
曲毕,赵濯灵不知不觉间落泪,她慌忙掩袖,以巾拭之。
俄顷,她抬头问:“彭伯,此曲叫什么?”
“回贵妃,此曲是为您《南望》一诗所作。”
“哦?《南望》作于永定三年,怎么现在为其谱曲?”
“回贵妃,犬子离京数年,《南望》写尽思亲之情,令人动容。”
“原来如此。”
彭伯低着头问:“贵妃近年来少有新诗,听闻您在写戏文,奴倾首竦耳以待。”
赵濯灵神色微动,“当年搬演《烂柯山》,你和宋娘子助力良多,如今她已离京,我的新戏也……也不知道何时写好。”
语罢,她敛眸,瞥向满儿,后者会意,扶她起身。
出了门,她低声道:“我要更衣。”
满儿笑,“奴知道。”
到了一间偏僻宫室,满儿推开门,自己并不进去,她知道赵濯灵如厕时不喜有旁人在场。
赵濯灵径往里走,忽见薄纱后闪过一道人影,滞步镇定道:“谁?”
大柱后走出一宫女装扮的妇人,穿着窄袖圆领袍和条纹袴。
“是你。”
妇人脊背笔直,双手交叠在腹前,施施然而来,“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