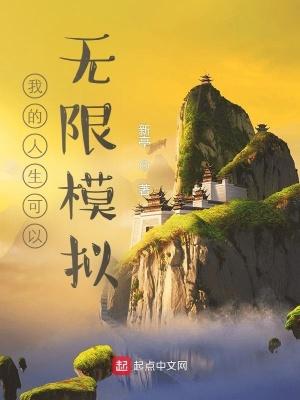笔尖小说网>锦衣卫他欠我一卦 > 钓鱼执法(第1页)
钓鱼执法(第1页)
是夜,北镇抚司除去当值的锦衣卫在正院集合巡查,其余地方都是静悄悄的,而北镇抚司的偏院,一片鸡飞狗跳。
“一万。”小侯爷掷地有声。
“二饼。”顾秉文神情专注。
“碰!”尤求找准机会,终于听牌,随即扔出边角料:“发财。”
“糊了!”沈落把牌一推,七小对,单糊发财。
尤求颤抖着把自己祖传的玉佩双手奉上,沈落利索的揣进怀里,正准备和众人说在打一把麻将就开始钓鱼,结果尤求清冷的脸上却顶着充满水汽的双眼。
“沈大师,这玉佩你可拿好,这是我母亲临终前给我的祖传玉佩,本来是传给我娘子的。”尤求满脸的不好意思。
“这都拿出来?”沈落咬牙切齿,愤怒的问:“这是能拿来输的吗?”
尤求抖抖自己干净的像刚制作好的荷包:“牌瘾上来,没有把持住。”
顾秉文站起声,表情冷的能把尤求冻死,拎起沈落,从这个守财奴的怀里把那块质地极佳的玉佩还给尤求,然后用冻死人的腔调对尤求说:“留着给你娘子吧。”
小侯爷在一边笑的像一只大鹅,他正准备从自己荷包里拿些银子接济尤求,结果他猛然发现就剩了一两银子,转头看沈落的荷包,一声怒吼响彻长夜:“沈落你荷包都撑吐了!”
顾秉文摸了摸自己的荷包,同样的所剩无几,而那位打麻将都要掐算一下的神棍,此时摸着那个撑吐了的荷包,脸上笑意止都止不住。
“如此看来,你们都没银子啦!”沈落挑眉,给每个人的荷包里又塞了二两银子,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说:“罢了罢了,怎么能竭泽而渔呢,还你们些。”
三个人在对方的脸上都看到了被羞辱的痛苦,哪怕是平时端的最厉害的顾秉文,此时也不由得漏出一丝郁闷,三人都把荷包扔到桌子上:“最后一把。”
沈落笑的满脸得逞:“我就知道你们三个得再来一把。”
一把过后,尤求吵着找绳子上吊,小侯爷拔剑准备抹脖子,顾秉文穿上披风准备找个水塘一了百了。
“别别别,咱们玩个新奇的,输一把脱一件怎么样?”沈落满脸的跃跃欲试。
尤求和小侯爷两个赌徒已经极度上头,正欲点头同意,顾秉文一人给了他们一脚:“你们的底线呢?怎能同意?不行!”
门外传来了锦衣卫去执勤的动静,整个北镇抚司的守卫骤减,此时只有固定的位置有执勤,四个人立刻转阵殓房,殓房有一个小隔间,是用作放置验尸工具的地方,装进去他们四个外加一个秋芷刚刚好。
五个人在小隔间里不敢说话,刚好有一个小缝看得清屋内,只听得见极其轻微的呼吸声,没过多久,一阵极其细碎的脚步声从房顶传来。原本还处于放松状态的众人,立刻紧绷,谁也不知道这条鱼,具体是不是他们要钓的。
沈落紧张的攥着顾秉文的胳膊,而顾秉文的肌肉也因此紧绷,蓄势待发的一只极度英俊的鹰犬。
伴随着窗户艰难的被打开的声音,沈落内心绝望的咆哮:这人非得走窗户吗,门都没锁,就窗户锁了!
这位极具个人见解的杀手,终于走进了殓房,四人眼睁睁的看着杀手伫立在没有锁的门前,静静将手掌握成了拳头,如果不是在北镇抚司,估计这个杀手一定骂得极其过分。
杀手回过神,看到墙上的人像,直接愣在原地,抬手抚过那张礼部尚书儿子的人像,众人几乎可以确认,这杀手就是人像本人。
桌上摆着的案件记录簿也被杀手注意到,他手有些颤抖的翻开,看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内容,他跪在了地上,无声的哭泣,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
沈落轻轻叹了口气,扶着秋芷走出了隔间,其余三人跟在了身后。
“你现在只剩下你的母亲了,你是谁的人,我可以暂且不问,但是你的母亲你不能不管吧?”
地上哭着的杀手把蒙面摘了下来,哑着嗓子说:“我该死,我杀了我的父亲和姐姐。”
秋芷听到这句话,踉跄着走了几步,流着眼泪跪倒在地上:“为何让我的家如此破碎?”
顾秉文走上前,抬手给了杀手一巴掌:“弑姐弑父之罪,你死不足惜。可你的母亲,被奸人所害,目不能视,你报了家仇,为你母亲养老送终,你再以死谢罪。”
沈落将秋芷扶起,带到杀手跟前说:“与你分离十八年的儿子,伸手摸摸吧。”
秋芷颤抖着手往前伸,杀手握住与他分离十八年的母亲的手,放在了脸上,二人都无声的流泪,太过悲伤甚至发不出声音。